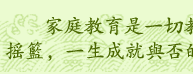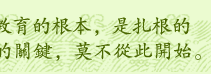我的母亲出生于一九三八年,今年七十五岁。不过按老人们的习惯,一般都讲虚岁,所以我母亲按虚岁算已经七十六岁了。
母亲十九岁嫁给父亲,二十岁生了大姐。在十五年间生了个八个孩子,基本上两年生一个。也就是每个孩子十月怀胎,然后大概养到一岁左右,就怀了下一个孩子。过去没有计划生育,所有结婚后的妇女一般都是顺其自然生,有的家庭孩子更多,听说有生十一、二个的。这样的情形一般是想要多生男孩,譬如说上面有十个女孩,只有一个男孩,所以拼了命想再生一个。
母亲所生的八个孩子,夭折了三个。其中最后夭折的是一个一岁左右的男孩。为什么这个男孩夭折了呢?因为在哺乳期间,我们家里的曾祖母病了,寒冷的冬天,母亲每晚要起来好几次照顾曾祖母,躺在母亲身边的这个男孩受了寒,患了哮喘。因家贫无钱医治就死掉了。
后来家里一直想还生个男孩,因前面几个活下来的孩子,只有老二是男孩,这在农村,家里没有两个以上的男孩,是不保险的。所以母亲又怀上了,这最后一个孩子就是我。一个女孩。
我出生于一九七一年,文化大革命中期。家里成分是地主,所以大姐没有能上完小学,她的同学都拿石头瓦块扔她打她,说她是「狗崽子」之类,大姐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回家务农了。而由于家庭成分不好,家境贫寒,我出生后并没有母乳吃,是母亲用米糊糊一口一口喂大的。
在家里最困难的那些日子,母亲曾看着这么多儿女每天张嘴要吃的,难过得流眼泪。奶奶劝她说:「每个娃就如一株草啊,沾点露水就能活。不要哭了,会过去的。」
这个「过去」大概用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,母亲用极其坚忍的毅力,忍辱负重,顾全大局,勤劳节俭,和父亲一起,带着五个孩子,将每一个艰难的日子过下来了。而且,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还有许多的欢乐。
我因为最小,所以获得了睡在母亲身边的权利。而小姐姐却只能睡在父亲身边。多少次,小姐姐哭着想要睡在母亲旁边,因为她害怕父亲,而我也害怕父亲,两人争夺的结果,最终都是因为我小,小姐姐要让着我,还是让我睡母亲旁边了。睡在母亲旁边,我经常偷偷地把腿搁到母亲肚子上,那肚子温软暖和。母亲一般都是任我搁着,但有时感觉沉了也会把我的腿推开,推开后我就再搁过去。母亲的肚子,是多么温软暖和啊。
等我稍稍长大点,母亲便开始教我劳动。首先从洗自己吃的碗开始。我们最小的三个女孩,每人都有一个小搪瓷绿花碗,用粗线沿碗边扎好再系上一双筷子。每顿饭吃完后,我们三姊妹就到河边洗碗,洗完碗后再挂在房间门的木柱子上。每当我们把碗洗得干干净净挂好,偶尔母亲正好看见,会笑眯眯地夸奖:「真好啊,洗得真干净。」那时,我们便感到很快乐。
再大一点,母亲便叫我捡柴禾。就是到树林里捡小树枝,那些大多是自然落下来的小树枝,干枯了用来烧火很好的。我很欢喜地到树林里去捡柴禾,无论捡多少带回家,母亲都会夸奖:「哦哟,好能干的孩子呢。一个鸡子四两力,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作用啊。」我问母亲,什么叫「一个鸡子四两力」?母亲告诉我:「牛的力气很大,鸡的力气很小,但各有各的作用。小孩子干不了大人的活,但是帮助做家务劳动也是很好的。」哦,原来我在这个家里,也很有作用呢。我非常高兴了。
家境的贫寒,以致每天的饭菜都很简单。米饭能吃饱就不错了,经常不能吃大米,而是要掺杂些碎米(富裕人家一般用来喂鸡的)一起煮饭吃。而菜,一年四季以腌菜居多。唯一能改善伙食的就是家养的鸡下的鸡蛋。母亲每次打一个蛋用清水搅拌好后,蒸上一碗。但这碗蛋雷打不动是家里的两个男人吃的——父亲与哥哥。我们可以等他们吃完后,将粘在碗壁上的零星蛋羹刮下来吃,但从不会要求或与父兄争吃。这是一个家庭的规矩,母亲用无言的行动让我们从小就明白长幼尊卑的秩序。
——未完待续——